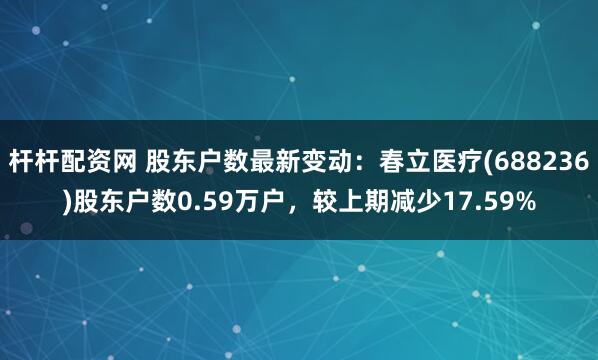“1943年仲夏夜杆杆配资网,皖江指挥部里灯火通明——’再多筹一万吨粮,我们就能撑过这个冬天!’曾希圣压低嗓音,却掷地有声。”这句在笔记本里反复出现的对话,成了后来无数老兵的共同记忆。彼时的新四军第七师,还被国民党情报部门当作“穷得叮当响的小部队”;可不到两年,他们却反手砸出一笔又一笔巨额银元,为整个华中局源源输血。钱从哪儿来?答案绕不开四个人的名字——曾希圣、蔡辉、叶进明、饶漱石。

先说曾希圣。湖南人,进过黄埔,也摸过情报暗线,心思灵活到让郝梦龄都头疼。抗日战争爆发,他被调去七师担任政委,带着一箱破译器材和一叠账目簿上任。刚到皖中,他就发现以往“打土豪”养部队那套玩不久,一打散,地方经济跟着瘫,自己也没地方买盐买布。于是他干脆把目光投向长江水道——日伪、汪伪、巨商、海盗、走私客全挤在这条动脉上,只要善用情报与算计,就能让敌伪的金库为我所用。“打不动的,就让他们掏腰包。”这是他对机关干部说的原话。
蔡辉出场则像商战小说。1943年春,他顶着“皖江贸易管理总局副主任”头衔潜回芜湖,公开身份是“军统特派员”,私下却为七师跑贸易。盐,是第一块敲门砖。当时皖南食盐每担被日军加征五道关税,粮商望而却步。蔡辉通过老同学杨大炎认识了伪维持会会长汪子东,先用两百石稻谷换来一船盐,又把盐运到郎溪换布,再把布送去敌后换大豆,层层加价,净赚三成。利润全部归进七师军需科,连一线战士都能按月领牙膏和香烟。更绝的是,他把所有账目都做成暗号,外人就算抢到帐册也只看到一堆“寿字”“福字”循环。
叶进明是“搬运工”兼“地下银行”。曾有人形容他“背着公文包跑前线”。他在南京、镇江、芜湖三地设了转运站,表面上卖的是鸦片替代品“医用樟脑”,实际上每条船的夹层中都藏着无线电元件、药品和枪机弹簧。为了保险,他让工人把银元熔成小锭融进锅底,运到目的地再重新铸回去。兵工厂师傅悄悄笑他太费事,他却说:“炸掉一条船,我至少还能捞出半锅银子。”正因如此,七师在1944年被日伪切断南北交通时,仍能一次性拿出200万美元面值的法币,稳住根据地市价。

若把七师比作机器,饶漱石就是那根让所有齿轮咬合的轴。他在华中局管组织、也管财经,人脉从闽南华侨到上海买办应有尽有。钱有了,人还得活着干活。他拍板在皖江后方建立三个炼钢小作坊、两家印刷厂、一处电台培训班。学员都是从占领区偷渡出来的大学生,三个月速成,当年就能把《拂晓报》印到敌后。更巧的是,饶漱石从海外搞来的侨汇大多是英镑与美元,他用这些硬通货在香港买机器,接着把发票交给叶进明,用假名“叶某”去南京中央银行兑成金条。金条被切割成两寸一段,夹入皮带扣子里,再经苏州、无锡一路北送。1945年七师北撤时,每位排长都分到一条这种皮带,后来在淮海战役前又被全部上交,用于统一后勤。
有意思的是,曾希圣最看重的并非银元,而是税收制度。他把盐、布、木材、煤炭列为“四大统税”,不问来源,只认重量。凡经皖江水道者,按百分之五到十缴纳通行费,收据盖“皖江行署”钢印。这纸收据后来成了整个长江中下游的通行证,连日军小队长都用它来走私私货。对我军来说,一张纸换来一车粮,比打下一座小城更划算。

有人质疑这是不是“灰色生意”。老战士回忆,曾希圣在1944年冬训上讲得明白:“谁若把账装进自己口袋,就是自废武功。”事实证明,严格监督加上丰厚补给,让七师在同年灵璧、泗县等战斗中火力配置堪比正规旅。那场大雪夜,迫击炮、重机枪交替压制,基层排长一声令下就能连续三小时不间断射击,这在抗战末期极为罕见。
战争尾声,七师把积累的巨额财富大部分上交华中局和军部,据赖传珠日记记载,“1942年底至1945年春,七师交现款五千三百万元法币,另有黄金二十六万两。”这些数字背后,是四个人将情报、贸易、运输与侨汇编织成纵横交错的网。试想一下,如果没有足够的盐、药、布料和枪弹,前线几十万人如何熬过最艰难的岁月?
遗憾的是,解放战争刚开局,四人已经分散到不同岗位再难聚首。有人说他们的故事像传奇,其实更像一部教科书——敌后经济工作、金融战、物资战,在七师身上被集中演练并推向极致。后来华东野战军那套“战场+工厂+市场”模式,正是源自这段积累。

如今翻检旧档,银元早已氧化发黑,布票也褪色,可在那些褪色纸片背后,仍能读到当年皖江水面上帆影交错、桅杆林立的繁忙景象。一个师,撑起几十万大军的口粮与弹药,这四个人实至名归。
尊富资本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